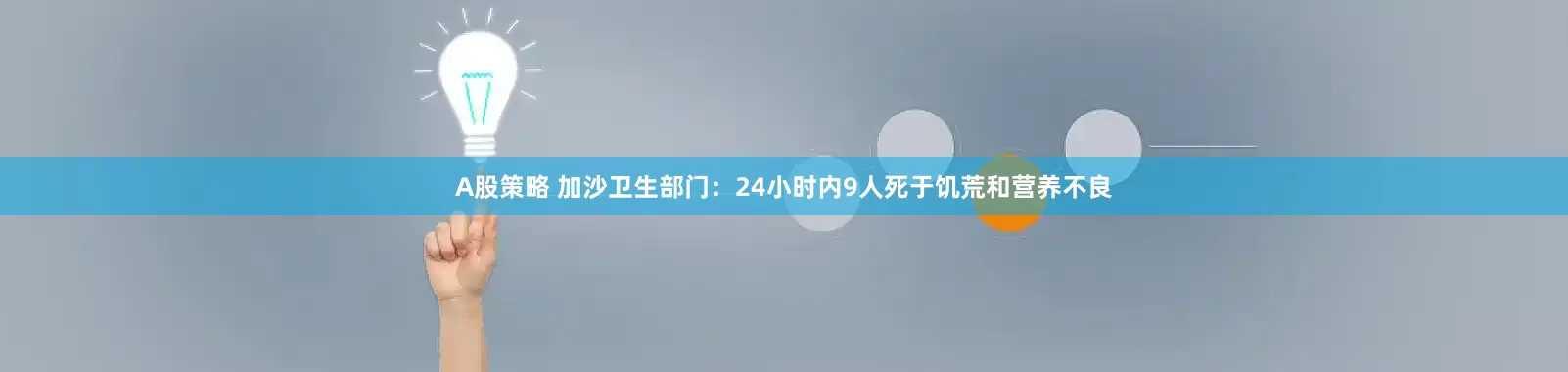路是真长。三十里土路恒瑞盈,坑坑洼洼,我推着这辆满载着“家当”和狼狈的破自行车,深一脚浅一脚。车轱辘时不时陷进松软的土里,得使点劲才能拽出来。铁皮箱子里的烤鸭随着颠簸,发出沉闷的碰撞声。
郑丽华走在我前面两三步远的地方,一直没回头,也没再跟我说一句话。她的红格子外套在傍晚渐暗的天光里,成了一个移动的、沉默的焦点。我只能看到她挺直的后背,偶尔因脚下不平踉跄一下时迅速稳住的身形,还有那条随着步伐规律甩动的大辫子。
风比来时更凉了些,吹得路边的白杨树叶子“哗啦啦”响。田野里暮霭开始弥漫,远处村庄的轮廓模糊起来,零星亮起了几盏昏黄的灯。
沉默像一块湿冷的布,裹在我们之间。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,车轮的“沙沙”声,还有她布鞋踩在土路上轻微的“噗噗”声。这沉默比刚才在街上的哄笑和质问更让人难受。它逼着我去想,去想我这混账的两个月,去想她那句“八年”。
我偷偷抬眼打量她。她个子在姑娘家里算高的,身形匀称,即使穿着厚外套也能看出利落的线条。小时候,她就是这十里八乡最俊的丫头,现在长开了,更是……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词:标致。对,标致。以前我咋就没这么觉得?光顾着烦她管我了。
展开剩余89%我记得有一年夏天,也是在这条路上,我们放学一起回家。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,辫子上系着红头绳。那天我偷了她爹地里的甜瓜,被她发现了,追着我打了半里地,最后还是分了她一大半,两人坐在田埂上,啃得满脸瓜汁,看着夕阳傻笑。
那时候,好像……没这么烦她。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大概是我初中毕业,不想念书了,整天想着往外跑,而她越来越像个“小管家婆”开始吧。她絮叨我穿衣吃饭,絮叨我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,絮叨我没个正形……我总觉得她像另一个娘,甚至比我娘还啰嗦,把我当不懂事的孩子。
可现在,走在这暮色四合的归途上,看着她沉默而固执的背影,我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,那些絮叨底下,或许……藏着点别的什么东西。是什么,我说不清,但心口那阵酸胀,又来了。
天彻底黑透的时候,我们村口的歪脖子老槐树影影绰绰地出现在了视野里。几点灯火在黑暗中温暖地闪烁着,偶尔传来几声狗吠。
快到了。我的心莫名地提了起来。
果然,刚走到村口第一家,正在门口收拾柴火的三婶就瞧见了我们,直起腰,嗓门亮堂地喊道:“哟!这不是丽华吗?这是……呀!大年?你啥时候回来的?这是……”
她的目光在我们俩身上,尤其是我那辆显眼的、散发着残余烤鸭味的自行车上,来回逡巡,充满了探究。
郑丽华停下脚步,脸上挤出一点笑,声音倒是很平静:“三婶,吃完饭了?大年他去县城进了点货,我刚碰上,就一起回来了。”
她说得云淡风轻,好像我只是去进了趟货,而不是躲了她两个月。
三婶“哦哦”了两声,眼神里的狐疑却没散,笑着打哈哈:“回来好,回来好!快家去吧,你娘这两天还念叨你呢!”
“哎,这就回。”郑丽华应着,不再多言,继续往前走。
我低着头,推着车,恨不得把脸埋进车把里。我知道,明天,不,也许今晚,我刘大年“落魄”地从县城被郑丽华“揪”回来的消息,就会传遍半个村子。
越往家走,遇到的人越多。好奇的目光,窃窃的私语,了然的笑容……像无数根细小的针,扎在我背上。郑丽华却始终挺着背,步伐不乱,遇到相熟的,还能神色如常地打声招呼,仿佛我只是她顺手捎带回来的一个物件。
终于,看到了我家那扇熟悉的、漆皮有些剥落的木门。院墙里,透出我娘做饭时灶膛里映出的暖光。
郑丽华在门口停下,转过身,终于正眼看了我一眼。暮色中,她的脸看不太清表情,只有眼睛亮晶晶的。
“到了。”她说,声音有些疲惫,“进去吧。”
我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羞愧,懊恼,还有一丝近乡情怯的茫然,堵住了我的喉咙。
她等了几秒,见我不动,也不催,只是伸手,帮我把自行车后架上松脱了一角的绳子重新紧了紧,动作熟练而自然。做完这一切,她拍了拍手,像是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。
“我回家了。”她说完,不再看我,转身走向隔壁她家那个同样亮着灯的院子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她推开她家的院门,身影融进那片光晕里,然后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了。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下来,只剩下我,和我这辆散发着油腻气味的破车,孤零零地站在自家门口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,推开了我家的院门。
“谁呀?”我娘的声音从灶间传来。
“娘,是我。”我低声应道。
脚步声急促地响起,我娘围着围裙,手里还拿着锅铲,从灶间跑了出来。看到我恒瑞盈,还有我身后那辆“标志性”的自行车,她愣了一下,随即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,有惊喜,有担忧,更多的是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无奈。
“你个死孩子!你还知道回来!”她举起锅铲作势要打,最终却只是轻轻落在我胳膊上,然后一把拉过我,上下打量着,“瘦了!在外面肯定没吃好!你说你……唉!”
我爹也闻声从屋里出来,披着外套,吧嗒着旱烟,看到我,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,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,没说话。
“我……我回来了。”我干巴巴地说。
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!”我娘抹了把眼角,赶紧帮我卸车上的东西,“还没吃饭吧?锅里还热着粥,娘再给你炒个鸡蛋!”
那一晚,家里的气氛有些沉闷。我爹没怎么搭理我,只顾闷头抽烟。我娘则不停地给我夹菜,问些“在外面受苦了吧”“住哪儿啊”“生意咋样”之类的话,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关于郑丽华的话题。
我食不知味,胡乱扒拉着碗里的饭。家里的灯光,娘做的饭菜香味,熟悉的一切,都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,但心底那份沉甸甸的愧疚和茫然,却挥之不去。
吃完饭,我帮娘收拾了碗筷,回到我自己那间久违的小屋。屋里还是老样子,只是蒙了一层薄灰。我躺在冰冷的炕上,瞪着黑黢黢的房梁,毫无睡意。
郑丽华红着眼圈的样子,她带着哭腔的质问,她沉默的背影,还有村里人那些目光……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转。
“八年……”我在心里又默念了一遍这两个字,翻了个身,把脸埋进带着霉味的枕头里。
第二天,我几乎没敢出门。我知道外面肯定流传着各种版本的“刘大年逃亡记”。我娘倒是出去了几趟,回来时脸色还算平静,只是偶尔看着我叹气。
快到中午的时候,我正蹲在院子里,心不在焉地修理一个旧板凳,院门被推开了。
是郑丽华。
她换了一身家常的蓝色碎花衣服,胳膊上挎着个竹篮子,篮子里放着几棵水灵灵的大白菜和一些针头线脑。她像是完全忘了昨天的事,神色如常地走进来,先跟我娘打了声招呼:“婶儿,忙着呢?”
“哎,丽华来了!”我娘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,脸上堆起笑,“快屋里坐!”
“不了婶儿,”郑丽华把篮子递给我娘,“我娘让我送点白菜过来,自家种的,甜着呢。顺便……我找大年有点事。”
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我娘连忙接过篮子,连声说“好好好”,然后给我使了个眼色:“大年,丽华找你,还不快去!”
我慢吞吞地站起来,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
郑丽华看了我一眼,眼神平静无波:“跟我去趟河边,帮我拿点东西。”语气不是商量,是通知。
我爹从屋里探头看了一眼,没说话,又缩了回去。
我只好硬着头皮,跟在她身后,走出了院子。
村里的土路在阳光下泛着白光。偶尔遇到村民,看到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,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郑丽华照样神色自若地跟人打招呼,好像我们只是寻常的未婚夫妻,正要一起去干点寻常的事。
我则像个鹌鹑,缩着脖子,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。
走到村后的小河边,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,只有哗哗的流水声和风吹柳条的声音。
郑丽华在河岸边一块大青石上坐下,也不看我,目光望着清澈的河水。
我僵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,等着她发落。
沉默了半晌,她终于开口,声音不高,却清晰地传入我耳中:
“刘大年,昨天的话,我没说完。”
我心头一紧。
“我等你八年,不是非要逼你娶我。”她依旧看着河水,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柔和,又有些倔强,“你要是真看不上我,真不愿意,你早说。我郑丽华不是没人要,不至于死皮赖脸缠着你。”
我喉咙发干,想辩解,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“可你啥也不说,就这么跑了。”她转过头,目光锐利地看向我,“你把我当什么?把你爹娘、我爹娘当什么?把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脸面当什么?”
她的质问一句接一句,像锤子砸在我心上。
“我知道,你嫌我管你,嫌我烦。”她扯了扯嘴角,露出一丝苦涩的笑,“可刘大年,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,我管你那些,哪一件不是为你好?你整天游手好闲,跟那些二流子混,能混出啥名堂?你去县城卖烤鸭,你以为你能成万元户?你那手艺,自己心里没数吗?”
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她说的,句句在理,句句扎心。
“是,我没啥大本事。”我憋了半天,闷声闷气地挤出一句。
“没本事可以学!”她声音提高了一些,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意味,“村里马上就要承包鱼塘了,政策好,肯下力气就能挣钱!王老五家去年承包的,今年就盖新房了!你力气不比别人小,脑子也不比别人笨,为啥就不能干点正经营生?”
我愣住了。承包鱼塘?这事我好像听我爹提过一嘴,但根本没往心里去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开这里,去县城,去更远的地方,好像只有那样才叫“闯荡”。
“我……”我哑口无言。
郑丽华看着我那副样子,似乎叹了口气,语气缓和了些:“大年,咱们都不小了。我不是要你马上有多大出息,但我希望你能像个男人一样,有点担当,有点正形。别让我……别让咱们两家人,一直这么提着心,吊着胆。”
她说完,站起身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
“话我就说这么多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”她看着我,眼神复杂,“你要是还想走,我不拦你。但走之前,把话跟我,跟两家人说清楚。别像个逃兵似的,让人看不起。”
她没再等我回应,转身沿着来路往回走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,心里翻江倒海。
河风吹过,带着水汽的清凉。她的话,不像以前那样疾言厉色,却比任何一次都更有分量,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。
逃兵。是啊,我可不就是个逃兵吗?逃避责任,逃避现实,也逃避……她。
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她的话。承包鱼塘?像个男人一样?正经营生?
我在河边那块大青石上坐了很久,直到日头偏西。
那天之后,我好像变了个人。不再整天想着往外跑,也不再躲着郑丽华。她偶尔还是会来说我几句,比如看见我衣服扣子扣错了,或者院子没打扫干净,但语气不再像以前那样冲,更像是一种……习惯性的提醒。
我开始跟着我爹下地,没事就往村里负责承包事宜的主任家跑,打听鱼塘的情况。我爹娘看我这样,脸上渐渐有了笑模样。
郑丽华有时会挎着篮子来我家,送点她家做的吃食,或者帮我娘做点针线活。她来了,也不多跟我说话,偶尔眼神对上,她就会迅速移开,耳根子却有点微微发红。
我发现,我好像……没那么烦她了。甚至,当她不再拧着我耳朵骂我,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家院子里穿针引线时,我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、安定的感觉。
一个月后,村里鱼塘公开承包。我鼓足勇气,跟我爹娘商量后,用家里仅有的积蓄,加上郑丽华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部分钱(她死活不说来源,只说是借的,以后要还),承包下了村东头那片不大不小的鱼塘。
签合同那天,郑丽华也去了,就站在人群里,看着我按手印。我没敢看她,但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背上,有点烫人。
按下红手印的那一刻,我心里忽然就踏实了。好像飘了很久的船,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岸。
而这片岸,似乎从一开始,就和她有关。
(第二章完)
#优质图文扶持计划#恒瑞盈
发布于:陕西省美港通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